陈政立(陈立典政和)
(原创)《砚床》打进了好莱坞
陈昌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不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甚多,屡有斩获。但谁都沒有想到,由地处深圳的中国宝安集团投资,初出茅庐的宝安集团影视公司和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攝制的第一部电影《砚床》,居然在上海第三届国际电影节上,被美国福克斯看中,购买了在欧洲部分地区的发行权,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打进美国好莱坞的中国电影。在第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第一次执导电影的刘冰剑和该片美术全荣哲分别获得了“导演处女作”和“最佳美术”两项提名奖,在深圳乃至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这部电影制片主任,参与了从筹拍到发行全过程亲历者的我,不仅完成了个人的第一次“触电”,也成功圆了作为老牌上市公司宝安集团和一群年轻人的电影梦,一个似乎遙不可及却又真真切切的好莱坞梦。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转眼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当年拍摄这部电影的那一幕幕往事仍恍然如昨,历历在目。
上马
我是1993年9月加盟宝安集团的,被聘任为主持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刚成立不久的宝安集团影视公司和跨世纪广告公司总经理。
那时的宝安集团正处于迅猛发展的扩张时期,号称“一大中心,九大总部”,覆盖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九大行业,在集团管理层运筹策划的未来发展规划中,文化产业已成为继房地产业、金融证券业、工业、商贸业后的第五大产业。宝安集团涉足影视产业起步虽不能算早,但还不能算晚。我在此时此地走马上任了影视和广告两家子公司的老总,足见集团高层对拓展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对我的希望及信任。
地处深圳的宝安集团总部
搞影视,我并不外行。来深圳之前,我在洛阳,干过五集电视剧《贴廓巷56号》的编剧和制片主任。后又当过十八集电视剧的制片。正是因为有拍过这两部电视剧的基础,我也才敢接手集团影视公司,而且第一把火,就准备烧钱拍电影。
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影视公司一成立首先招兵买马。我先招聘了一个来自长影的二级导演许传臻,接着又招聘了一个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攝影刘冰剑。这俩一个正规军,一个科班,听说我们要拍电影,都兴奋不已,跃跃欲试。那段时间,我一方面主持宣传部工作,-创办《宝安风》杂志,一方面四处撒网,组建影视队伍。在北京钓魚台国宾馆召开中国宝安集团发展战略研讨会时,我们还聘请了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戚健导演,亲自为研讨会全程录像。由于不能马上拍戏,戚健沒呆多久就离职了。多年后他执导了电影《花季.花季》,成了导演大腕。我们还跟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导演吳天明,有过密切联系和接触。吳天明那时刚从美国回国发展,第一站先到深圳寻求合作,对宝安集团影视公司很感兴趣。集团的陈政立总经理亲自出面洽谈合作,因集团未能接受吳天明提出的“干股”比例,沒有达成协议,失去了一次十分难得的合作机会。倘若那次谈成合作,凭借吳天明的名气,和在中国电影界的影响,宝安集团的影视产业想做大做强,应该不在话下。可惜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过,已经招聘了一个专业导演,一个专业攝影,加上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制片,又有集团的资金保证,拍电影应该可以上马了。
筹拍
兵马未动,剧本先行。拍电影首先得抓本子。早有准备的刘冰剑帶来了一个现成的本子。这是根据安徽作家李平易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一篇获奖小说《巨砚》改变的电影剧本《砚床》,编剧是李平易的朋友,叫程鹰。
剧本《砚床》主要描写徽州一偏僻山村的一座深宅大院里,瘫痪多年的老太太独守着祖上留下的一块巨大的石砚打发着难耐的时光。应该说,片中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氛围都是十分深厚的。
凭借过去多年文学创作的积淀和对几部电视剧拍摄的经验,我对这个剧本感觉很有文化底蕴,富有民族特色,便把这个项目报给了集团投资部。当时的投资部长毛利本是北京来的一个厅级干部,投资经验和人脉资源都很丰富。他先把剧本寄给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朋友,请他对剧本提出意见,又让我们找深圳电视文艺创作中心进行把关。这两个来自不同渠道的专业机构,对剧本的评判大同小异,都认为题材不错,也有基础,可以立项。但在找谁出任导演的问题上,毛部长和我有较大分歧。他认为这是集团投拍的第一部电影,为保险慎重起见,应该找一个拍过电影的老导演。而我出于剧本是刘冰剑带来的,又是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的两方面考虑,不妨让他一试。从投资角度分析,毛部长的意见是对的。从艺术角度分析,新人可能有冲劲,一度僵持不下。我还曾到毛部长北京的家中和他沟通交换意见。说到情急之处,我还以张艺谋为例,说他就是摄影出身,现在不成了红得发紫的大导演,来说服毛部长。岂料毛部长闻言勃然大怒,竞对我下了逐客令,令我好不尴尬。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找集团领导决断。
《砚床》导演刘冰剑
陈政立总经理原则同意了我的意见,却明确提出了该电影必须收回全部投资的硬性指标,算是把我逼上了梁山。 之前在洛阳拍的那两部电视剧,有政府投资,有企业赞助,只要正式播出,就算完成了任务,从来没有要求经济回报。 这一到深圳,一进企业,游戏规则就全变了。 为了确保收回投资,集团还要求我和刘冰剑签下军令状,如果不能收回投资,将酌情扣罚我们的工资。 这一招够厉害的,让我们领教了企业拍电影,可不是拿钱让你烧着玩的。
值得庆幸的是,《砚床》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主管全国电影生产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专门为《砚床》增拨了一个故事片拍摄指标,在下达的批复文件中这样写道:“剧本通过一方流落民间的皇家巨砚展开的故事,表现了当代普通人对历史文化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的态度,显示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依恋与追求。剧本在努力开掘文化内涵的同时渗透了许多现实生活的清朗气息,并注意人物塑造和形式美感的营造。经过努力,可望拍摄一部立意健康、艺术品位较高的作品。”
作为联合摄制一方的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素以敢于在艺术上创新而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新上任的厂长金继武出任本片出品人。而宝安集团的领导更是高度重视。董事局主席曾汉雄和总经理陈政立亲自出任总监制,陈总还多次指示我们,片子选准后,要抓紧,不拍则已,拍就一定要拍好,第一炮务必打响!
为了确保艺术质量,我们专门聘请了著名导演滕文骥担任该片艺术指导。筹拍期间,我们又专门到北京,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尹鸿教授等一批影视专业人士,对剧本进行讨论修改,并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在读硕士林黎胜执笔,集中大家提出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一些补充修改。特别是剧务主任陈胜利对剧本最后结尾的修改意见,推开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砚盖,将原来是一些花纹改为是长工阿根被害的遗骸,可谓之笔点睛,老太太苦苦厮守了一生的砚床,才有了更加令人信服的依据。
回头来看,我们对《砚床》剧本的敲定和论证修改,对电影的立项和审核,都是必要和科学的环节和流程。战舰开始出航,当然也是试航。我们希望它能抵达目的地。但途中难免会遇上风浪,碰到暗礁。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中途返航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只有按预定的航线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彼岸才会越来越近。
开机
汽车在坑坑凹凹、蜿蜒曲折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砚床》剧组驻扎的外景地——黄山市管辖下的休宁县五城镇。从南京到黄山,坐了大半夜火车,下车来已是凌晨四点,正是千金难买的黎明时辰。不仅我睡不成,也搅得剧组的剧务和司机,不得不从七十里之外赶来接我。又赶上大雾,车灯的光束,怎么也穿不透那笼罩着夜色的白茫茫雾障,司机开得分外小心。
车到驻地,天已放亮。这是个还比较贫穷、落后的边远小镇,离举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还相距200多公里。镇上破旧的房屋居多,一些颇有气派的深宅大院还是当年外出谋生的“徽商”积攒钱财后盖起留下的具有明清风格的建筑。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也是剧组之所以选中此处作外景地的原因。
剧组人员住在据说是镇上最好的镇政府招待所。房间内除了床、桌子和登子,别无它物。简陋的居住环境倒能忍受。要命的是不能洗澡。全镇没有一个澡堂。这可苦了摄制组这帮想干净也干净不了的演职员,还常常断水。原来自来水是抽到水箱里再放出的,一早一晚工作那么一阵子就“罢工”了。剧组只得一周拉到县城来那么一次周末大清洗。
此地物价也并不低,吃饭并非众口难调,招待所雇请的厨师,手艺着实令人不敢恭维。尽管如此,大伙的情绪还颇高。几天相处,没听到有人抱怨,更多的是在谈论怎样拍好戏,怎样加快进度。有个剧务调侃道:“既然我们是为艺术而献身,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献身虽说是玩笑,但也不纯粹是玩笑。有些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可谓大矣!
刚当母亲不久的邓烨,撇下才几个月的宝宝,干起了制片;扮演青年男子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付鹏程刚风尘仆仆赶到五城,家里就打来电话,最心疼他的祖母去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他返家见了祖母最后一面又赶回组里继续拍戏。摄影组人手紧张,摄影师李雄除了一天到晚把机器外,还得亲自搬运摄影器材。美工组长全荣哲在和大队人马同时到达的紧迫压力下,凭借扎实的功底,迅速搞出了整个设计的盘子。影片《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照明师张树斌和李兴全共同担任照明组组长,张树斌里外忙活得团团转。而李兴全一会儿摆弄测光表,一会儿调度灯光,他同时还兼任着副摄影。
曾在影片《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荣获第十二届金鸡奖最佳道具的八一厂道具师刘清斗,为了赶制剧情需要的大砚床,不得不用木炭烘烤来促其快干,和另一个道具刘长青天天烟熏火燎。化妆李雨就一个光杆司令,清晨一大早给演员化妆,还得盯现场。导演刘冰剑和场记蒲剑同住一室,天天拍摄结束后仍无法休息,开完主创人员会,研究完第二天的计划还得为一个个镜头的筹划熬到深夜。
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李滨和天津人艺的老演员肖林,均已届花甲之年,本应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又拼着把老骨头来饰演戏中的老太太和老古董师。在翻箱倒柜寻找过去物件的爬楼梯一场戏中,老太太不顾年迈,在老宅子破旧的楼梯上爬了几个来回。在场的人无不为她捏一把汗,可她胳膊都磨破了,仍全然不顾,直到爬得导演满意为止。
出演老太太的北京人艺老演员李滨
一群为艺术而献身的执着的人们!
与休宁相邻的黟县南屏,是张艺谋拍摄《菊豆》的地方。 聪明的黟县人,不仅凭借着老祖宗留下的那片古朴的明清建筑,吸引、招徕着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也巧妙地利用了张艺谋的名气,打出《菊豆》故乡的招牌,更平添了几分诱惑。
《砚床》剧组到达休宁后,导演刘冰剑曾带领摄影、美术等主创人员到黟县选景,来自八一厂的美术全荣哲看了南屏后,不由得惊叹,保存得这么完整的明清建筑,实在是太罕见了,岁月沧桑,光阴流逝,时代变迁。居然没给这片建筑带来什么损坏,那老宅子、那石板路、那小巷、那院落,浑然一幅三四十年代的南方风情画,完全符合剧情的要求,无需做更大的改动和加工。难怪张艺谋、陈凯歌这些红极一时的“大腕”们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刘冰剑老是抱怨,由于他们合拍片的资金优势(这两年张、陈的片子,基本是海外老板出资,他们执导),催动了这一带拍片的行情见涨,厮守着那些老宅子的乡亲们,才猛然醒悟,这不起眼的老宅子也是“宝”,招惹得摄制组走了一拨,又来一拨。敢情拍这些老宅子也要钱。过去是花钱买票看电影,如今是拍电影的找上门,还得倒找钱。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场租费、劳务费、镜头等等这些电影术语,也越来越频繁地挂在乡亲们的嘴上。
在此之前,刘冰剑曾只身前来选景,已被当地老乡开出的价码惊得咋舌,才不得不从黟县转移到还尚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休宁。而外景的效果,自然差了不少。但是,休宁没有的外景,还得到这地方来。比如,那幽深的小巷,那斑驳的石板路,不到此,就拍不出那味道。不得已,还得硬着头皮来。
不来不知道,一来就领教。那些早被拍电影吊高了胃口的村民们已很有经验,哪些要收钱.该收多少,早给你算计得清清楚楚。更使人大开眼界的,是在拍老古董师独自走过小巷的镜头时,导演让看热闹的几个小孩,从小巷跑过去。增加一些气氛。谁知剧务上前商量了半天,那几个小孩就是不动。待剧务哄他们跑完后给他们买糖吃,还是没反应。剧务急了,问他们要什么,一个孩子伸出一个手指,原来是要钱。剧务哭笑不得,赶忙答应。随着导演一声令下,几个孩子非常听话,叫啥时跑就啥时跑;叫怎么跑就怎么跑。显然,他们已不是看到摄影机还觉得新奇、好玩的儿童了。很可能,他们是从大人们那儿得知,剧组让这么“跑”是应该付报酬的。
无独有偶,当剧组又转移到另一个外景地——万安拍摄时,遇到的事更邪乎。这是陈凯歌执导的《风月》选定的外景地。因女主角易人,拍了一部分镜头后暂时搁下了。《砚床》剧组前来,虽无《风月》轰动,但规矩是早已有先例的。当摄影机选取镜头时,发现一家老乡窗外的衣服“穿帮”(拍摄术语,即多余的人或物进入拍摄镜头),需要取下,赶忙派剧务前去交涉,谁知央求半天,就是不肯取下,非要十元钱,才肯“高抬贵手”。剧务忍气吞声,只好花钱开路。还不敢声张。怕其他老乡也起而效仿,纷纷挂出“万国旗”,何以了得。“大团结”也真灵,那老乡钱一到手,就笑眯眯地将衣服取下。
《砚床》剧照
如此收钱,倒还罢了。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些“痞子”乘机前来“敲竹杠”。在万安拍完之后,要走时,从一位老乡家将存放的服装取走时,那位老乡倒通情达理,没说什么,三个当地的“小痞子”说啥不让走,非要剧组掏“存放费”、“安全费”才放行。那位老乡连说“算了!算了!”“小痞子”还是不依不饶,无奈。只好又用“大团结”了结。摄制组实在是搭不起时间,不敢多纠缠。
领教了厉害和尝到了滋味的演职员们,连声惊呼“世风坏了”,我倒颇不以为然。除了敲竹杠的无赖之外,乡亲们“要钱”,看起来是给拍摄加大了开支,增添了麻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块偏僻之地,却因拍电影而启发了乡亲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倒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
常在报刊上看到这样的口号:“要致富,先修路。”我看倒应改为:“要致富,换思路。”因为只有换了脑筋,有了思路,才有可能无路修路,无桥搭桥。然而漫天要价、无理取闹也是令人不愉快和不足取的。这就又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正应了老人家在世时的语重心长的教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愿我们的《砚床》也能起到这么一次教育作用。
补拍
在我们的期盼和等待中,《砚床》终于完成了前期拍摄,开始进行后期制作。万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回到深圳的我,接到了影片艺术指导滕文骥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影片剪辑完成后,由于拍摄的素材不够,影片的长度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先不说影片质量,连最低的合格水平都达不到,一下惊出了我的一身冷汗。我在办公室呆坐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看来,正应了投资部毛部长并不多余的的担心,第一次拍胶片的刘冰剑犯了最低级的致命失误。我想起了在开机时,和滕导在休宁的见面,他当时要求刘冰剑“素材一定要多拍多拍,哪怕是空镜头”,免得到了剪辑时,长度不够,到那时哭都来不及了。刘冰剑可能年轻,并没有当回事,现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我赶紧给螣导打电话,问他怎么办?他说,你赶紧来北京,商量对策。我立即飞到了北京,和滕导、刘冰剑一见面,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砚床》的出路只有一条——进行补拍,要把剧组的全班人马悉数召回,重回休宁补拍镜头,这意味着跟重拍一遍差不了太多,劳民伤财不说,那些演员和主创人员有没有档期也是大问题。这简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如果补拍,影片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如果不补拍,影片必死无疑,前期投入的拍摄资金就将全部打水漂,又该如何向集团交代?

听着滕导的利害分析,看着刘冰剑的后悔莫及、一筹莫展,我倒冷静了下来,补拍困难重重,不补拍死路一条,只有追加投资,进行补拍,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我立即赶回深圳,向集团领导进行汇报,在我的力主下,集团同意追加投资,进行补拍。我又立马飞回北京,亲自主持补拍事宜。经过再三商议和论证,我们决定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搭设内景地进行补拍,省却剧组重回休宁补拍的鞍马劳顿和大批资金。镜头全部补拍室内戏,只要美术、置景按照原来的场景进行恢复,尽量避免“穿帮”的痕迹,应该问题不大。
听说补拍,剧组工作人员大都好说,只是一些演员有些过分,他们知道,补拍非他不可,坐地抬高了价码,我们也只好认了。好在大多数演职人员都还通情达理。为了改变表现过去历史时空的内容份量过轻的毛病,我们又找专业人员充实剧本内容,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重新搭设了摄影棚,补拍了大量过去时空的镜头,从而使影片的整体水平和艺术质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好事多磨,几经周折,我们总算顺利完成了全部补拍。
《砚床》剧照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补拍和后期制作完成后,又出了场署名风波。 小说《巨砚》的原作者李平易要求署名编剧,参加过剧本讨论的制片邓晔和执笔修改大家意见的林黎胜也提出来挂名编剧。 考虑到后者毕竟执笔做了些修改,在原来稿费的基础上,我们又补签协议,增加了些稿费,进行了了结。 对于参加剧本讨论就要署名,那参加讨论的多了,怎么可能? 至于李平易,解铃还须系铃人,就请导演刘冰剑出面调解,毕竟他是小说作者和编剧的中间人和见证者,一场编剧风波就此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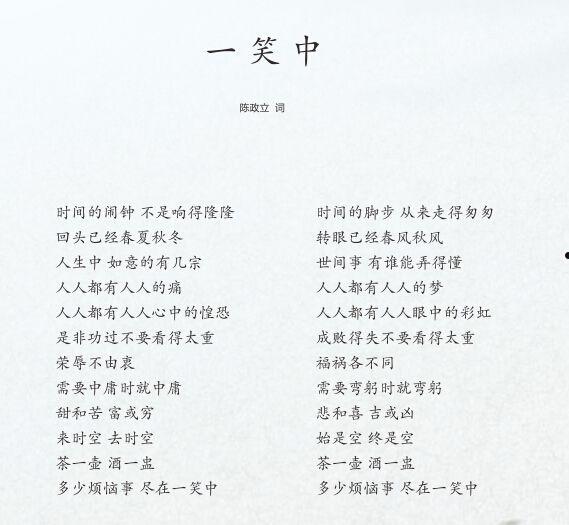
青年制片厂的合拍部张主任,听说我们在不长时间内解决了这场署名风波,深感佩服,据他的经验,这种由署名引起的版权纠纷,搞不好就会影响电影最后的审批,陷入旷日持久的折腾煎熬之中。
圆梦
为了早日收回投资,我们在电影《砚床》的后期制作时,就开始了市场发行的前期调研。刚刚完成演员对白的录音后,中国电影公司的有关人员看到后,就产生了浓厚兴趣,向导演刘冰剑提出了购买全片的要求。我得知后,向集团领导作了汇报。那时正赶上集团要归还五个亿的企业可转换债券,急需资金回笼,就要求我们只要能收回投资,可以出售。我当即安排剧务周宏亮和中影谈判。几个回合下来,中影方面在我们的报价下,提出再压十万元就可成交。周宏亮担心别为了十万元影响成交,因小失大。倒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只是凭直觉中影仅仅看了录音对白的初剪片,就下决心购买,怎么会在乎这十万元的讨价还价。果不其然,电影《砚床》最终顺利成交,我们收回了影片的全部投资。
在此期间,还有个小插曲不得不提。当时的万科影视,在国内影视圈名气很大。我拿到《砚床》的对白录像带后,曾去找老总郑凯南和副总王培功征求意见,他们看完,听说中影愿意购买,认为可以成交,不要犹豫。对于搞企业影视的过来人来说,他们的专业意见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饰演 少爷、少奶奶 的 演员 傅程鹏 和 陈 颖 映
1997年的金秋十月,是个收获的季节。上海第三届国际电影节传来消息,由宝安集团影视有限公司和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中国电影公司发行的彩色立体声故事片《砚床》,继1996年台湾片商购买了台湾市场代理权后,1997年10月26日下午,在上海银星假日酒店,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与中影签约,购买了《砚床》在欧洲部分地区的发行权。这也是建国以来美国好莱坞购买的第一部中国电影。上海解放日报以“好莱坞首次购买中国拷贝”、文汇报以“中国大片美国放映”、新民晚报以“美国片商纷纷购买中国影片发行权”为醒目标题,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它标志着国产影片出口业务获实质性进展,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又有了新的突破。
影片《砚床》讲述的是—个令人回味,非常惨烈的故事。在徽州偏僻山村的一座深宅大院里,瘫痪多年的老太太独守着祖上留下的—块巨大砚台。古董师的到来,引起老太太对往事的回忆,几欲收购砚床的古董师成了她能说点儿心里话的人。但古董师并不了解老太太真实的内心世界。平时照顾老人起居的远房侄媳妇也不真正懂得老人为何对砚床如此痴恋。侄媳暗中答应把砚床卖给了别人。当买主把沉重的砚盖一寸寸地推开后,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砚盖下压着当年少爷为了借种,让少奶奶与长工偷情,结果又惨遭毒手的阿根的尸骨。为了那段尘封在砚床里的痛苦而又令人窒息的岁月,老太太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饰演 长工 的演员史 鑫
影片选中的安徽黄山脚下的休宁作为外景地。历史悠久的徽派建筑,美丽迷人的自然景物,浓郁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清新脱俗的文化品味,以及过去那个年代复杂扭曲的人性与当今时代各色人等对砚床的不同视角,构成了这部影片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尤其是影片推开砚盖,让老太太苦苦死守一生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的结尾,令人震惊,撼人心魄,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令人欣喜的是,《砚床》在艺术和市场的追求上,达到了比较完美和谐的统一。在1996年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脱颖而出,导演刘冰剑和美术全荣哲分别获得了导演处女作奖和最佳美术奖两项评委会提名。导演刘冰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连续拍摄了多部电影,最近的新作是完成了京剧《定军山》的拍摄,为中国京剧树碑立传。重回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全荣哲更是成了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的常客,最近一届获奖是《狼图腾》。
《砚床》美术全荣哲
《砚床》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是推出了两位过去默默无闻的影视新人。第—次拍胶片扮演长工阿根的史鑫,由《砚床》出镜,已成为出演《浴血太行》和《长征》等影视剧,当今影视界颇为走红的、饰演青年邓小平、仅次于卢奇的二号演员;扮演少奶奶的陈颖映拍完《砚床》后,又出演了电视连续剧《叶剑英》元帅夫人的角色,从而引起影视界瞩目。担任剧务的许漫天,拍完《砚床》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留校后当了教师,还成了一名专业编剧,可谓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砚床》是成功的,它凝聚着深圳和宝安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艺术和市场的结晶;《砚床》是幸运的,它在不经意间,打开了世界电影著名的殿堂——好莱坞的大门;《砚床》是慷慨的,它圆了一群年轻人执着而又苦苦追求的电影梦。
探询《砚床》成功的秘诀,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那句名言。《砚床》的突破和追求,再次给先生的论断增添了最好的注脚。
2019年7月14日
标签: 陈政立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